阐述旁观者效应总结:数字时代的历史发展和相关性
引言:旁观者效应是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人(即旁观者)的存在会影响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帮助他人的可能性。具体来说,随着出现紧急情况的人数增加,任何一个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心理学史上发生的一个关键事情是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协会 (SPSSI) 的成立。在 1936 在该组织成立之前,心理学领域并不涉及研究和应用心理学原理和研究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不相信心理学领域可以从事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并且仍然是一门科学学科。
然而,在大萧条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心理学可以应用于解决国外和国外的社会冲突,时代精神开始发生变化。事实上,自 SPSSI 成立以来,心理学家一直专注于应用心理学,通过观察群体动力学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
一、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与理论:情境因素、动机因素和旁观者效应
深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的勒温也对研究影响一个人行为的情境因素感兴趣,这导致他发展了场论。他认为,一个人所处的情境是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方式的新的决定因素。
此外,卢因在 1950 年代对行为动机影响理论的贡献使社会心理学家推测是什么促使他人参与亲社会行为。这种对动机因素的关注是 1950 年代出现并延续到 1960 年代的“认知革命”的特征。认知方法侧重于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展开全文
这种对认知的关注对于试图理解指导个体在群体中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家来说至关新的。虽然当时的社会心理学家对影响一个人帮助他人的动机的因素很感兴趣,但研究问题在 1960 年代转变为是什么导致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不向某人提供任何帮助。这种转变是由 1964 年的一起妇女被谋杀悲惨事情引发的。
一项研究反映了心理学家试图研究可能影响旁观者效应发生的因素;具体来说,这些研究人员将匿名性作为旁观者效应中的中介变量进行了研究。这两项研究都代表了 1980 年代通过操纵可能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旁观者数量以外的因素来进一步测试旁观者干预的努力。
瓦伦丁的目标是调查可能削弱旁观者效应的因素。她认为,如果旁观者和受害者之间形成了积极的联系,那么旁观者可能会觉得更有必要帮助受害者。根据 瓦伦丁的说法,在旁观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最佳方式是实施人际凝视,在旁观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眼神交流。
因此,瓦伦丁假设无论旁观者是否在场,受害人的凝视都会增加参与者的帮助行为。为了测试凝视对旁观者效应的影响,瓦伦丁在实验室外进行了一项实验。
她指示一名同盟者(无旁观者条件)或两名同盟者(两名旁观者条件)在纽约指定的公交车站接近随机女性。
二、社会心理学中的“旁观者效应”的两项实验研究的介绍和分析
一名同盟者会“不小心”把口袋里的所有零钱都弄丢了,而另一名同盟者则站在附近看报纸。之后,掉落硬币的受害者要么注视参与者,要么盯着地面五秒钟,然后捡起掉落的硬币。当参与者捡起掉落的硬币或指向他们在地面上的位置时,就会发生帮助。
瓦伦丁发现凝视确实影响了参与者的帮助,正如预期的那样——处于凝视状态的参与者比没有被凝视的参与者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并且帮助更快(无论旁观者的数量如何)。瓦伦丁的研究不同于达利的研究,因为她没有测试紧急情况下的旁观者效应。
相反,她使用自然环境(现场实验)并使用掉落的硬币来表示受害者需要帮助。她的目标是通过引入以凝视为代表的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既定联系的干预因素来削弱旁观者效应。而且,瓦伦丁并没有使用超过两个旁观者。
虽然可能很难想象一个简单的凝视会导致旁观者和参与者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但这种实施背后的目标是确定凝视是否会引起对受害者的义务感,这将迫使参与者参与帮助。
牢记瓦伦丁研究的这些方面,可以评估该研究的有效性。在结构有效性方面,明显操纵的自变量(凝视与不凝视和一个同盟者与两个同盟者)反映了研究中的高结构效度——她准确地操纵了理论结构。
因为这是一项实地实验,而不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研究人员无法控制所有的外来变量,这意味着她的研究的内部有效性很低。例如,她无法确保在实验进行时没有其他人会来到公共汽车站,因此,引入了一个混杂变量。
尽管存在这个问题,瓦伦丁还是训练她的同伴在参与者面前表现得几乎完全相同,这表明她试图尽可能地保持事情不变。关于外部有效性,由于仅选择了白人女性参与者,该研究被削弱了。
它不会推广到其他参与者群体,例如男性和其他种族/族裔背景的人。然而,因为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环境,所以具有很高的生态有效性,因为实验是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当受害者进行某种形式的接触并承认旁观者时,旁观者效应不太可能发生。
在瓦伦丁发表她的结果的同一年,施瓦兹发表了他们对影响旁观者效应发生的其他因素的调查。施瓦茨和戈特利布提出,旁观者的匿名性可能会影响他或她是否帮助受害者。作者声称,除了达利描述的责任和责备的扩散之外,另一种可能影响帮助的力量是评估忧虑。
这种解释与旁观者是否知道其他旁观者和受害者是否知道他或她的存在有关。施瓦兹推断,感觉自己是匿名的旁观者不太可能帮助受害人,因为他或她的评估忧虑较少。
为了检验个人感知到的匿名性使得个人不太可能在明确的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的预测,施瓦茨和戈特利布用非常复杂的程序进行了两个复杂的实验。他们的第二个实验基本上复制了第一个实验的结果;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只描述他们的第一个实验。
他们第一个实验的实际参与者到达社会科学大楼的一个房间,并被指示通过在电视屏幕上观看另一名学生的超感官知觉 (ESP) 传输来监控他。电视屏幕上的学生实际上是一名专业演员。从表面上看,演员正在将 ESP“传输”给另一名学生,该学生应该在另一个房间接收 ESP 消息,参与者看不到。
ESP 实验开始大约 7.5 分钟后,屏幕上显示的学生在遭到“衣着粗鲁的陌生人”(也是演员)的人身攻击时成为受害者。两个自变量被操纵:旁观者的存在和匿名。施瓦茨和戈特利布通过单独带领参与者来操纵目击犯罪的另一名旁观者在场或不在场有条件相信收到 ESP 消息的学生迟到了并且在犯罪时没有注视受害者。
此外,施瓦茨和戈特利布操纵了参与者是否相信他或她是匿名的还是已知的。在匿名条件下,参与者被引导相信其他学生(即受害者和 ESP“接收者”)不知道该研究涉及多个参与者;在已知条件下,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在 ESP 实验结束后与所有其他学生(即受害者和/或其他 ESP 接收者)会面。
由于这项研究采用了析因设计,每个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四种情况之一:(1)在单独/匿名情况下,参与者认为他们与受害者单独在一起并且受害者不知道他们在场;(2) 在单独/已知情况下,参与者认为他们与受害人单独在一起并且受害人知道他们在场;
(3) 在旁观者在场/匿名条件下,参与者相信另一个旁观者在场,并且参与者对受害者和其他旁观者都是匿名的;(4) 在旁观者在场/已知条件下,参与者相信另一个旁观者在场并且参与者不是匿名的。
施瓦兹复制了达利结果,因为他们发现旁观者在场会降低参与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施瓦兹还发现,与他们的预测相反,参与者对受害者的匿名感知(即单独/匿名条件)并不影响参与者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
然而,为了支持他们的预测,当参与者认为他们对受害者是匿名的并且另一个旁观者(即旁观者在场/匿名情况)。施瓦兹认为,这些结果与他们的主张一致,即评估忧虑以及责任分散有助于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
施瓦兹扩展了达利的研究,通过操纵感知的匿名性,或者一个人认为没有其他旁观者知道他或她的存在的个人感知,并发现匿名缓和了旁观者效应。施瓦兹在他们的研究中很好地操纵了匿名性,正如参与者对用作操纵检查的实验后问卷的回答所表明的那样。
例如,96% 的参与者正确回答了关于他们是否希望在 ESP 实验后与其他学生互动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与达利的研究类似,外部效度低,因为它不是代表性样本,因为它只包括本科生。
然而,他们的研究具有良好的生态有效性,因为它是在参与者在电视屏幕上听到和看到紧急情况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与达利实验中仅从录音带中听到的声音不同。
瓦伦丁和施瓦兹是 1980 年代的两项杰出研究,代表了心理学家在不同条件下调查旁观者效应的努力。
他们确定其他变量,如凝视和感知的旁观者匿名会影响旁观者的干预。在开展这些研究后的 20 年,研究人员开始追求更具应用性的研究目标。例如,他们开始将旁观者效应应用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欺凌行为也相应增加。
2000 年标志着与在线情况相关的旁观者干预研究的开始。例如,马基盖尔对在线聊天网站中的亲社会行为进行了研究。马基盖尔在聊天网站 Yahoo! 上观察到数百个聊天组。
他张贴了各种帮助解决计算机问题的请求(例如,如何在线查看某人的个人资料);有些请求是针对所有聊天组成员提出的,而有些则是通过引用他们的名字针对特定成员提出的。
然后,他监控谁回答了问题并提供了帮助。马基盖尔发现当有更多人登录到聊天组时,成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响应。但是,当问题针对该组的特定成员时,情况就相反了。虽然马基盖尔没有像达利那样进行处理紧急情况的实验,但这项研究揭示了网络世界中旁观者效应的临界边界;
将问题直接针对另一名成员,具体说明成员的姓名,这样就更有可能做出回应。因此,它抑制了旁观者效应。这可以追溯到瓦伦丁的研究,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凝视或对旁观者的认可使旁观者更有可能进行干预并提供帮助。
虽然这不是紧急情况,但未来的研究人员承担了研究在涉及网络欺凌的情况下如何存在旁观者效应的任务。自马基盖尔以来,心理学家开始感兴趣的一个更突出的社会问题是网络欺凌。自马基盖尔研究以来的 16 年里,布罗迪表明,网络欺凌是一个与我们现代社会相关的社会问题。
这些研究人员通过要求调查参与者描述他们目睹的朋友过去的在线欺凌经历,对旁观者数量与感知匿名性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布罗迪发现受害者对旁观者数量的感知与干预的可能性(通过李克特式评定量表衡量)之间呈负相关。
也就是说,随着感知旁观者数量的增加,干预的可能性会降低。他们还发现,旁观者的匿名性与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当旁观者是匿名的时,他们不太可能提供帮助。然而,这些相关性不是实验结果,只能解释为关联,而不是因果联系。尽管如此,这些发现可以被视为旁观者效应和匿名性(以及旁观者效应的减少)研究的延续。
三、笔者认为
从历史上看,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的成立、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及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以及认知革命的出现,都为研究为什么没有旁观者干预以帮助一名女性在纽约州铺平了道路。
旁观者效应在 1968 年由达利首次通过实验证明是一项经典研究,它改变了未来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在达利之后进行的研究调查了影响助人行为的其他变量。
此外,21 年初上个世纪标志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心理学研究与当代社会问题的相关性,在线聊天室和社交媒体网络欺凌等情况下的旁观者效应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综上所述,显然达利和拉塔内关于旁观者效应的经典研究仍然与现代心理学领域高度相关。
参考文献:
1.鲍迈斯特, 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Sage 出版社,2007年。
2.本杰明,《现代心理学简史》,新泽西州霍博肯:威利,2014年。
3.达利,和拉坦, B. 《紧急情况下的旁观者干预:责任分散》,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1968年。
4.穆克 《心理学经典实验》,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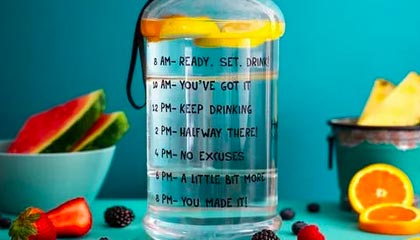






评论